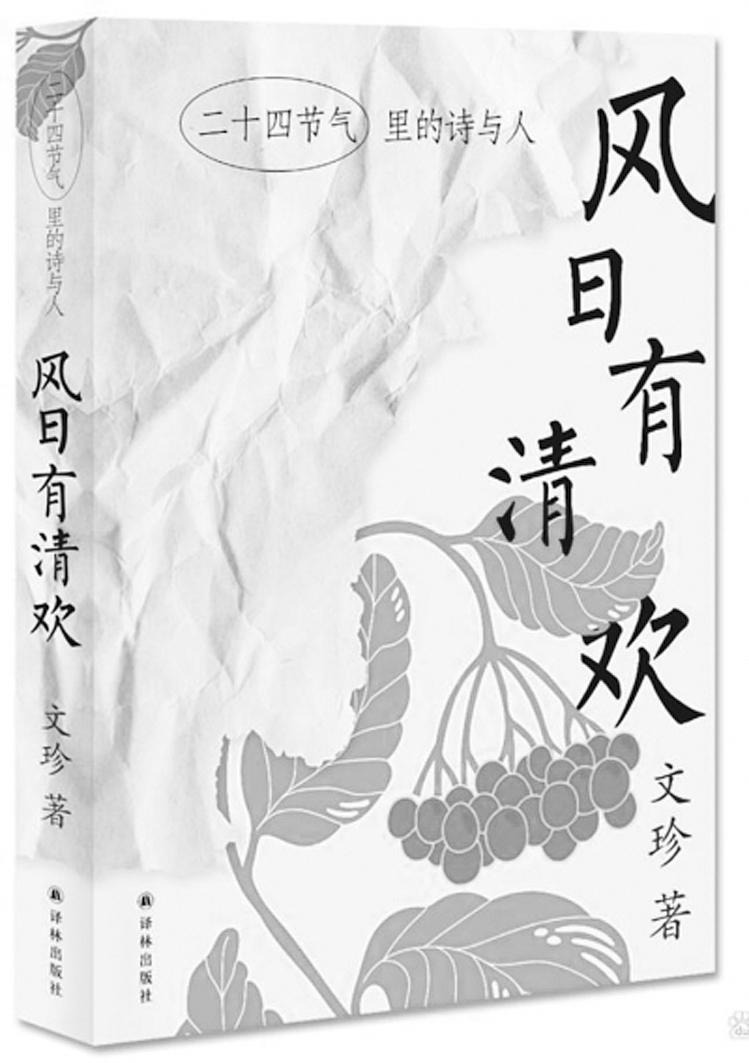文珍的这本散文集《风日有清欢》有一个副书名,“二十四节气里的诗与人”,译林出版社又把书装帧得非常古雅。第一眼看《风日有清欢》,我以为这是一本老气横秋的怀古之作,也就是说,这是一本古人因二十四节气而生发的各种情绪之作的大汇合。这么解读,似乎也不错,文珍以元代文人吴澄编著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为底本,下足了稽古的功夫,将她觉得最好的——对应二十四节气的古诗词,从立秋至大暑排列在文章的字里行间。
这样一本资料翔实的散文集,读完也不舍得插进书架而是被我放在手边,夏至未至、秋意渐浓、凛冬已逝、春风又绿江南岸的时节,我想我都会拿出《风日有清欢》来,重温。
过去的和远方的诗人留下的能让我们感慨节气的诗行,经由文珍的起承转合,如点点繁星让一本书处处发散着光泽。然而,我敢肯定的是,假如再读《风日有清欢》,我依然会在那些折射出内心褶皱的日常细节面前驻足更久。
霜降,是秋天最后的节气。言说到“最后”二字,语气里便有了告别、至少是暂别的况味。从宋朝诗人郑刚中的诗里拈出两句“霜作晴寒策策风,野鸟相呼柿子红”来引领霜降这一话题的文章中,文珍选择了白居易的五言诗《岁晚》确定了这一节气的“言下之意”,全诗的最后一联“何须自生苦,舍易求其难”,白居易感慨的当然是被贬南方五年不能回家的无可奈何,可文珍更愿意从这首诗里汲取的,是前一联“去国固非乐,归乡未必欢”里苦中作乐的情怀,所以,她愿意腾出时间来在一个深秋、风已经很冷的周末,去到远离北京城的皮村给一群文学爱好者上课。
那段被选印在辑封上郑刚中两句诗下的文字扑面而来:“我们却总还忍不住去舍易求难,踮脚去够那月亮,不过因为在活着之外,还有一点点喜欢”,它当然是指生活在皮村的进城务工人员何以爱上文学的原因,可又何尝不是文珍的自我写照?她之所以愿意在霜降时节不畏初寒地来到皮村谈文学,是因为“天真蛮勇地以为一切会因自己的努力变得更好”,而她,又喜欢当一个自己喜欢的人。
喜欢当一个自己喜欢的人,更喜欢自己喜欢的人们。从2019年起写作的这一组主题关于节气的文章,到2021年完成最后一篇《大暑》,历经了两年有余,无论是立秋、处暑、白露、秋分……还是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只要一想到与酷暑严寒、春花秋月相关的人和事,文珍一下笔便是那些她喜欢的人们。
二十四节气,只是古人为气候变化做的标注,本没有高下之分,但相比之下“惊蛰”是一个招人欢喜的节气,因为,《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关于惊蛰的三候分别为“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倒有二候与鸟鸣相关,也就是说,是黄鹂和布谷叫醒了我们的耳朵、告诉我们春天来了——被寒冬腊月苦苦纠缠着的人们,谁不期盼春天快些来呢?
所以,文珍写到《惊蛰》时,也是诗兴大发,一口气在文中嵌入了三首与惊蛰息息相关的古诗。三首诗中,无论是文珍认定古人中写惊蛰最好的陆游的那一首,还是仇远和舒岳祥的佳句“野阔风高吹烛灭”和“细筛微雨落梅天”,都有一种意气风发的气象,非常豪迈。然而,这一篇《惊蛰》文珍写到的日常,却是她二伯遽然过世的过程。理应悲伤逆流成河,但文珍更在意的是让读者像她一样喜欢她的二伯,于是一个有趣的二伯跃然纸上,失去的悲伤从而让位给了对一个人的喜欢。
以二十四节气为名,记录的其实是文珍喜欢的日常和在文珍的日常中进进出出的她喜欢的人,这就是《风日有清欢》,一本以日常细节描绘内心褶皱的散文集。
来源:光明网